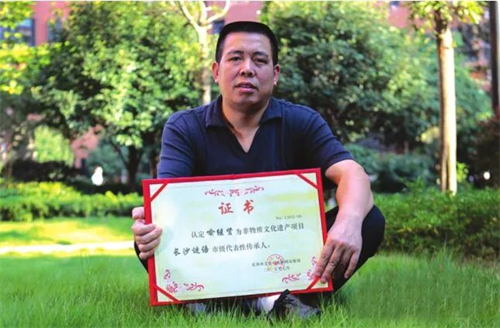◎李传思
驼子你无论前看后看,左看右看,都像一只立着的河虾。然而,驼子长得好看,娃娃脸,亮眼睛,皮肤桃花色,而且聪明,有灵气,特别会编歌,会唱歌,在李家村周围几十里好多人喜欢。听大人们背地里议论,莫看驼子比别个矮一截,动作也比别个慢几拍,但好多婆娘就喜欢他。他是可惜了,背上比别个多个包,好多赚工分的活做不得,屋里穷得没间像样的屋,所以三十多了,还光棍一根。
他在生产队负责看牛,住也住在牛栏边一间又小又黑的屋里。打我有记忆起,他就没爷没娘。听奶奶说,他爷老倌以前是个补鞋的牛皮匠,在过苦日子时死了。他娘受不了穷,又因崽是个驼子看不到希望,丢下他走了。他是生产队把他做五保户照顾长大的。生产队还送他学剪脑壳,还给他配了个工具箱。农闲的时候,他就背个箱子到附近几个村喊“剪脑壳嘞,剪脑壳嘞”。一毛钱一个脑壳,赚点钱。本村的人去他牛栏屋找他剪,八分钱一个。也因为这个缘故,驼子在远远近近很有点名气。
那些牛特别听驼子的话,只要他的那根看牛棍往哪个地方一插,说:“在这里呷啦。”很奇怪,牛们都只围着棍子周边呷草,绝不乱跑,像孙猴子用金箍棒划圈一样神奇。而驼子要么在边上睏大觉,要么靠着树唱自己乱编的歌。
我在光明山捡完松树叶子回屋里,经过山下那块草地时,正听到驼子在唱歌:
昨夜哥哥去妹家
妹妹见哥心情欢
巫山云雨一下下
明年小儿见天光
我不晓得他唱的么子家伙,只觉得像我们那一带普通的山歌,因为调调我熟悉。我从他身边走过时,喊了声:“驼子叔”。
驼子哎一句,说:“猫伢子,捡柴去了?”
我说:“嗯。”
他问:“你晓得我唱的么子不?”
我说不晓得。
他挤挤眼问:“想晓得不?”
我说:“想。告诉我。”
驼子把我牵到一边坐着,好像呷了碗肥肉那样脸上放光:“好,我告诉你。有个女的,结婚几年就是不生崽,要我帮忙。你莫看我驼起个尸,身体好嘞,而且聪明,她们都喜欢我。昨天夜里,那个女的喊我睏了一觉,我保证她明年会生个胖崽子。我刚刚唱的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我就笑,似懂非懂。睏一觉就生得崽出?我问。他更来劲了,说:“你没看到隔壁胡家村有个老倌子,经常赶头猪到我们村来?”
我点点头。
驼子说:“那头猪是专门来我们村给生产队那些母猪生崽的,叫脚猪。我就是脚猪。你懂吗?”我还是似懂非懂。
驼子似乎急了,说:“下次我去别个屋里做脚猪,带你去好不?有肉呷嘞。”
我点头,想起有肉呷,心里就放肆挖。
他高兴了,说:“好,到时我喊你,不过那要搞到好晚才回得来。你怕不?”
我说:“不怕。”
过了些天,有个下午,驼子到我屋里对我娘讲:“嫂子,我到谭家村去看个妹子坨,我想带猫伢子一路去。”
在我们那里有个规矩,去看妹子坨的总要带个人,好像伢子妹子单独一起会犯罪似的,或者说不好意思。不像现在,伢子妹子都想方设法单独一坨,恨不得直接那个。所以现在看,那时带个人就是带个道具,以做掩护。当然,要带的一般都是细伢子,既是个人,又不懂事,他们照样该做么子做么子,就像我是空气一样。
我娘同意了。她说:“这是好路,你带猫伢子去吧。不过,早点回,太夜了细伢子怕舍魂。”
驼子说:“放心罗,我会把他送到屋门口的。”
我们约好时间。四点多,驼子来了。我跟他走。他先把我带到他牛栏屋里,说:“我看你头发好长巴长了,要剪下,好看些。”
我说我没钱。他说这次不收你的钱。
我听话地坐在他屋前的树墩上。他拿来一块黑不拉矶油光发亮的剃头布系在我颈根上,开始给我剪脑壳。此时太阳正西斜,暖洋洋地晒在身上。有头牛在他脚边走过来走过去,哞哞喊着,好像在喊哪个同伴耍,尾巴啪啪打着自己屁股,那里苍蝇蚊子一堆。驼子剪脑壳的技术非常厉害,不仅又快又好,就是推剪子的声音都与众不同,嚓嚓嚓地,像个温柔的弹棉花匠在弹棉花。他还有手绝招,是挖耳朵。哪个剪脑壳,哪个都央求他来一下。他挖耳朵,痒痒的,酥酥的,你不会怕,只感到舒服得要死。一会,一粒老鼠屎样大小的耳屎在你快乐的享受中噗然而出。
我因为没钱把,不好意思提要求。驼子善解人意,问:“猫伢子,好久没挖耳朵了吧,有坨好大巴大的耳屎。”
我向往,说:“是的咧,夜里睏觉翻边就响,火得死。”
驼子从工具箱里取出个点油的东西,像把壶,点了几滴放我耳朵里,凉凉的,像条虫往里面爬。然后他用根细长的勺子伸进里面掏,先听到訇訇响,接着是空空响,那家伙在里面一出一进,痒得我一身轻飘飘,快活得神仙似的。突然,他嘿地一声,一粒珍珠样的耳屎被他捏了出来。我顿时觉得神清气爽,通体轻灵。
驼子说:“去,到塘里洗个脸,擦下颈根头发,准备走喽。”
我就去塘边用手把脸搓几下,又把颈根上的碎头发抹掉。驼子这时收拾好了。我们上了路。
谭家村离我们村子比较远,走了一半,我脚巴子实在抬不动了。
驼子说:“来,我背你一截。”
我爬到他背上,刚走几步还好,但走久了,我的肚子总觉得是被哪个的膝盖顶着一样难受。驼子背上那个尖家伙太硬了。我吵着要下来,要他抱。驼子也可能晓得原因,不得不抱我。但前面抱个人,对他来说实在太累,时刻往前面栽似的。走了一截,他气喘得拉风箱一样。
我见了,不忍心,说:“我好多了,我自己走吧。”
砣子高兴,说:“还是猫伢子懂事。快到了,有肉呷了。”
听到肉字,我似乎闻到了喷香的肉味,脚像上了风,走得飞快,搞得驼子在后面一颠一颠喊:“等下我,等下我。”
太阳落山时候,我们到了那个人屋里。那个屋里只一个婆娘,年纪和驼子差不多,在等我们。屋里有张呷饭的桌子,桌子那边是张床铺,铺上有床蓝色印花被子。她见我们来了,好热情的,先端出南瓜籽和落花生,泡了茶,叫我们呷,然后去了后面的灶屋。没好久,她真的端肉出来,满满一碗,放了青辣椒,香得我鼻子喉咙都伸出了手,肚子一下空了。
“饿了吧,走古远巴远的路,来,我们呷饭喽。”那个婆娘还筛了一茶杯米酒放到驼子面前。
驼子唆了口酒,呷了块肉,好享受地怪叫一声。
那婆娘说:“我屋里男人出去了。他一再喊醒我,要好好把你服侍好。请你一定帮他搞个崽出来。”
驼子把胸部拍得咚咚响,说:“落一百个心喽,我帮的到现在还没有不成的。”
那婆娘兴奋地说:“我听说了,讲你好神的,而且生的都是伢崽子。”
驼子得意地又唆了口酒,说:“那倒不是吹的。”
酒足饭饱后,驼子抹下嘴巴说:“猫伢子呷饱了不?”
我以为他要走了,站起来说:“呷饱了。”
他挤了挤眼睛,笑道:“你还有样东西没呷的。”说着,把他的杯子放到我面前说:“这酒好呷,喝了有劲,回去就不要我抱了。”
那婆娘瞟他笑,又瞟我笑,似乎在问我敢不敢喝。
他们都不晓得,在屋里我爷娘平时不准我沾酒,酒坛子用布包着放床底下,拢边都不准我拢。可我经常等他们出去,偷偷喝几口。久而久之,一点酒想把我搞醉,那是做梦。于是,我满身豪气,端了驼子剩下的酒一饮而尽。不一会,我还是感到脸发火烧,眼睛前面的东西都在打圈圈。不过我有点晓得他们的用意,想把我搞醉,我就故意把脑壳往桌子上一伏,装作倒了,但闭上的眼睛朝向床铺。我想等下我随时可以看驼子叔是怎么做脚猪的。我觉得好耍。
我听到那个婆娘轻轻问:“细伢子睏了没?”
驼子笑道:“嘿,落心,肯定几个时辰不得醒。”
听得两人嘻嘻嘻地上了床。我眯开一线眼睛,看到那个婆娘脱得白花花躺在那里。驼子叔也脱得光光的,像只煮熟了的虾公。那婆娘哧哧笑:“你这个驼子,看倒秀秀气气的,家伙却嚇死人。快,快点。”
我不敢再看。奶奶讲过,看大人床上打架会得铁钉子(麦粒肿)。我把那线眼睛闭上了。也怪,那一下就睏着了。
不晓得过了好久,驼子喊我。四周没点声音。他说:“猫伢子,起来,要回去罗。”
我迷迷糊糊跟他出门上路。沿途走了好久,我不记得了。我只记得那晚的星星好多巴多,挤密挨密;只记得驼子一会吹口哨,一会唱歌,一副快活得要死的样范。
妹妹无崽心里慌
哥我今夜来帮忙
山高水浅哥欢喜
保你来年有儿郎
歌声在寂静的夜里,广袤的乡间,显得格外嘹亮。我牵着他的手,跟着哼,跟着哼,跟着就到了屋门口。
有次我从河里挑水回屋里,看到驼子正赶着队上的几头牛,准备去河对门呷草。我照例喊声:“驼子叔叔。”
驼子尖到我边上,像抓着个好大的秘密,对着我耳朵说:“你叔下的种发芽了。”
我莫名其妙望他。他看我没懂,觉得好笑,说:“明天我又要去当脚猪,你去不?”
那有么子味罗,一点都不好耍。我摇摇头:“我明天有事。”他有点失望,走了。不过只一会,远处就传来他好听的歌声:
哥哥是天天有雨
妹妹有地地孕谷
天下雨来地滋润
地长禾苗家幸福
回头望去,我看见驼子正骑在一头粗壮的牛背上挥舞棍子,扭动屁股,像个常胜将军,在朦胧的天幕下,显得特别高大,似乎那尖尖的驼峰一下消失了。
名人热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