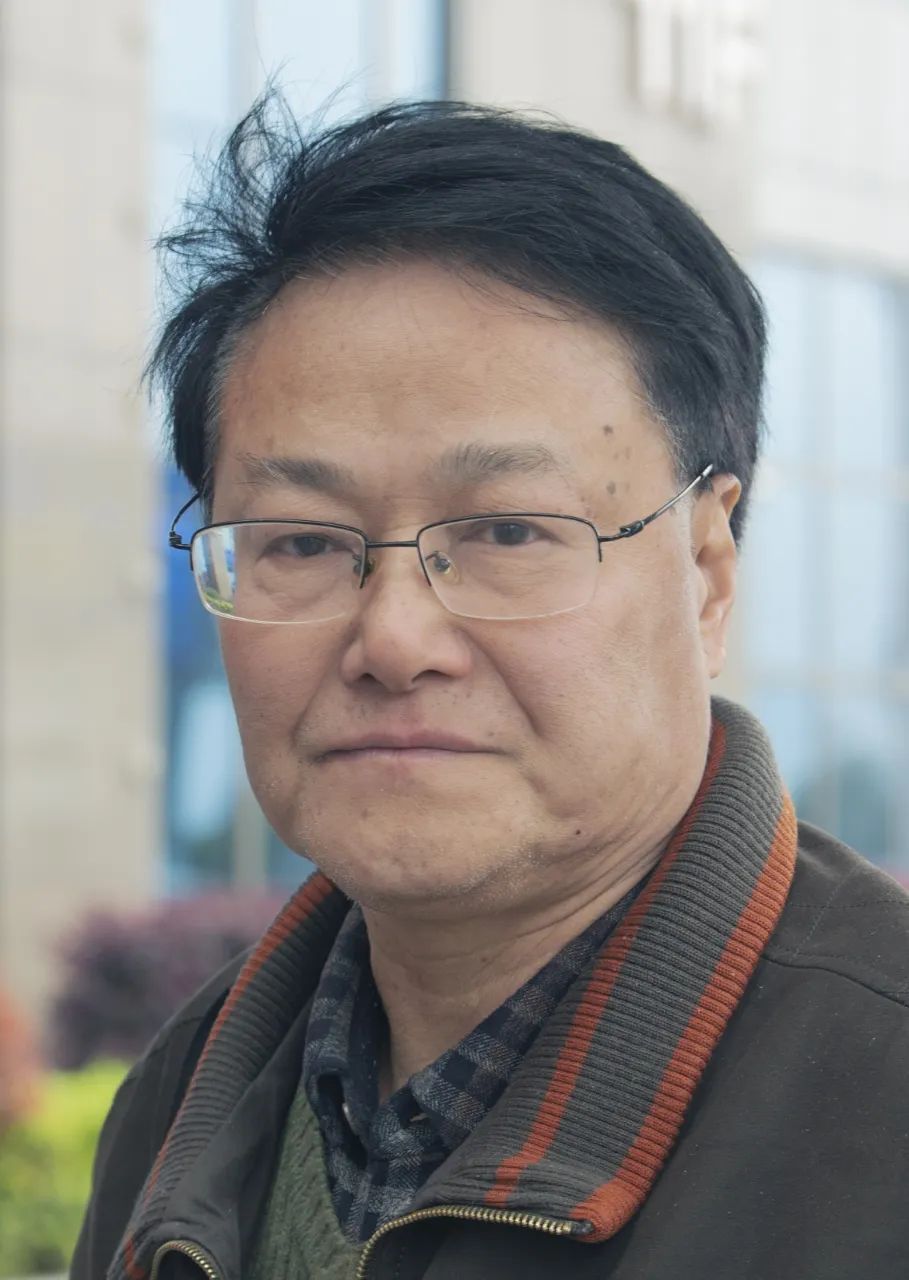◎万宁

一
黄嘴巴与黑嘴巴是我从集市里买回来的。
四月的集市气象万千,有一长溜是卖菜秧、花苗、果树苗的,还有一长溜是卖鱼苗、鸡崽、鸭崽与鹅崽的。这天,一位擤着鼻涕、穿得跟包子样的四岁女孩站在一个大筐前,亮得出水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筐里使劲扑腾的一群鸭崽。
我紧挨着女孩蹲下去。女孩看了我一眼,又掉头看鸭鸭,她眼中,我只是个与她一样看鸭子的人。
“烂便宜,烂便宜,一百块钱八只。”胖墩墩的老板娘对着空气吆喝,又不时瞟我一眼,瞟得我脑门冒汗,我紧了紧嗓子,挤出声音“我买两只”。
这回女孩足足看了我两秒钟。她那黑黑的双眸射出两道正在舞蹈的火焰,这火焰在我的脸颊上温柔地舔舐。老板娘扔给我一个红色大网袋,我把网袋撑开,对女孩说:“帮我选两只。”
女孩没吱声,胖手手早已伸进鸭崽群,鸭崽“叽叽”地向一边闪躲,胖手手在空中犹犹豫豫,手伸向这只,她又觉得旁边的那只好,如此反复,她一只也没抓上。最后,她狠了狠心,在众多鸭崽中捞了一只,小心放进网袋里,接着又捞了一只,这次,她捧在手掌上,嘴里喷出的热气弄得鸭绒毛颤动不已。
忽然一个喊声,女孩松了手,她被人拎起背背衣上的布结,走上斜对面一家米粉店的台阶。老板娘的目光跟了过去,抿着嘴儿兀自笑,“这孩子,一天不知要来多少回,她妈妈店里的事都做不完,哪会给她买鸭鸭玩。”
越不买就越惦记。鸭鸭的萌样儿会在小孩子的心房里住下来,就像我家的茉莉。
在这个春天的集市里,我又买下鸭笼子,拎着它们,就像拎着春天回家了。鸭崽鸟儿般的叽叽声,撒了一路。放到院子里的草地上,它们挤作一团,嘴里仍在叫唤,当然它们叫归叫,却抱着跟定了我的决心。我停,它们也停,保持着一米的距离。
家里的九妮从屋里奔出来。它是一只十岁的泰迪,一直待在城里,鸡崽鸭崽倒是见过,但见到的通常是玩具。此刻,九妮愣在原地,双眼鼓得老大,竖起的耳朵一颤一颤,鼻子朝空气里擤了擤,然后嘴里叽哩哇啦地自说自话。当然也就短暂的一会,九妮便开始情绪激动,它冲了上去,低下头去嗅它们。两只鸭崽咿咿呀呀仍在呱噪,且乱走乱动,九妮有些困惑,一时无法判断它们是来自哪里的物种。九妮随着它们摆动身体,呆萌半天后,它伸出右脚,试探性地“啪”了一下。一只鸭崽被拍翻在地。鸭崽发出急促的惊慌声,它们遇到了鸭生之中的第一次危险。
与所有动物的本能如出一辙,它们迅速逃跑。
它们缩在墙脚,九妮跟了过去,用它的身躯挡住了鸭鸭所有的逃生之路。鸭崽蜷曲在一起,斜着眼睛,身体哆嗦得上下起伏。我实在看不下去,朝九妮吼了一声,九妮停下抬起的前爪,迟疑了半会,悻悻地掉转头,跟在我后头。

二
我种菜,鸭鸭跟在我脚边,我一靠近,它们又躲开,躲得没地方了,它们就挤在墙角瑟瑟发抖,好像我虐待了它们。不过,我倒是真想扑它们几棍子。刚来时,它们只是跟脚。我在跟我,我不在,它们就跟别人,于是时不时跑到别人家。
十几天后,它们不跟人了,而是跟人作对。
它们把我种的丝瓜、南瓜、香瓜还有藤蕹、红薯秧子吃了个精光。这些菜秧好不容易躲过早春的寒冷,躲过一直下的绵绵春雨,才长稳了根。只是万万没想到,终究没有躲过鸭子的嘴。
我是赶早种下这些菜秧子的,只想着早春耕、早收获。种下后,我剪了好几个大桶矿泉水瓶,一下雨或者气温一降,就盖上这些瓶子,让它们在瓶子内躲雨避寒。这天是个晴好的日子,早上我把所有盖在菜秧子上面的瓶罩取了,黑嘴巴与黄嘴巴正在草地里翻泥、捉虫子,对我用切碎的菜叶搅拌的米饭不屑一顾。我赶着进城,随它们自由觅食。在城市里奔忙了一天,临近黄昏,两只小鸭的黄色绒毛居然在我心窝窝里撩拨,该要给它们喂食了。
心急火燎地踩着油门往家赶。家里寂静无声。门一开,九妮扑过来撒欢,我敷衍着它的激动,直奔后院。开满花的柚子树下,黑嘴巴黄嘴巴正脸对脸趴在一块,长长的细脖子环出一颗温暖的爱心。夕阳的余晖穿过枝上白色柚子花的缝隙,落在鸭鸭身上。柔风拂动,花儿的浓香在空气里炽烈、奔放,我停住脚步,闭上眼睛使劲嗅,试图要把这浓香植入记忆深处。
香味儿散漫出丝丝缕缕的气息,黏附在身体的某个角落,我心满意足。睁开双眼,两只鸭子摇摆着身体绕到食盆前,开始啪唧啪唧地吞咽食物。我的目光越过它们去看我的菜地。诡异的是,我陷入了一个荒诞的梦境,泥土上的菜秧子消失殆尽,这块土地仿佛从未耕种过。
菜园子里空荡寂阒,醍醐灌顶的风盘旋而至,刹那间,明白了一件事实。
我尖叫一声,“臭鸭子!”吼声从胸腔里爆发。顺手拿了根竹棍,扬起我无法遏制的愤怒。鸭鸭奔跑起来,翘着屁股摇摇晃晃的,踱起的方步看着又四平八稳。
我在后边追了一阵,又忍不住想笑。它们挤在墙角的京九红下,嘤嘤地叫唤,我用竹棍敲了敲靠在墙边给京九红爬藤用的支架,邦邦声响一下,几片京九红花瓣落了下来,鸭鸭缩紧的身体就哆嗦一下,然后又歪着脑袋斜着眼睛朝我偷偷看过来。
三
“奶奶,你恼啥呀”茉莉从北京打来视频电话。每天瞅一眼鸭鸭,是她的固定节目。“奶奶,鸭鸭的大脑只有半个球,你比它们多半个球,你的功能比它们多好多,它们能惹上你吗?”
无论鸭子犯了啥事,小姑娘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鸭鸭一边,所有的不是都扔给奶奶。
说起来黄嘴巴与黑嘴巴是茉莉要买的。
还住在城里时,我带她去公园玩,她最来神的项目是套圈。花花绿绿的玩具摆满地面,在一根画线后边,她卖力地朝目标丢圈,说到底她的目标就是那几只呆萌的活小鸭。站在一旁看她丢圈,圈圈落地的那一秒,我总是心惊胆颤。
万一丢中了,她这是要带回我家养的。养过的人都知道,鸭鸭到了家,不是正在拉粑粑,就是在拉粑粑的路上。
我最幸运的事莫过于茉莉从未丢中过,尽管看着她难受委屈,我也挺难受的,但我心里的窃喜与庆幸还是忍不住在脸上晃悠。
边上小男孩丢中了。
茉莉艳羡的目光黏了过去。鸭鸭抓过来时,茉莉伸手想摸摸,男孩屁股一扭,转过身子,用他那还不宽阔的臂膀护着他的鸭鸭,生怕茉莉这一摸,就会摸走鸭鸭的羽毛。茉莉的手僵在那,放下来后,就左手掐住右手,眼眶里有泪水打转转。
我赶紧拉住茉莉的手,“走,我们去百鸟馆,喂鸟儿去。”给鸟儿投喂,茉莉也喜欢。此刻,她的脚步没有迟疑,跟着我走,只是眼睛还在往那男孩手里的鸭子瞟。
我拍了拍她的小脑袋瓜,“你真喜欢,那下次奶奶给你买两只。”
茉莉停下脚步,仰起脸,眼睛里的光亮,剔透晶莹,她反转身子,另一只手拽了过来,带着兴奋摇晃我,“真的吗?是真的吗?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图嘴巴痛快,迟早要出事。这个时候,想改嘴已来不及了。
我蹲下去,琢磨着用拥抱来安抚她。茉莉推开我,定定地望过来,“奶奶,是真的吗?你会给我买两只小鸭子吗?”
清澈的目光空前威猛,我竟然鬼使神差地连连点头,含含糊糊地说:“等奶奶搬到乡下住,咱就养两只。”
茉莉笑靥如花,天边的新月也跟着荡起笑意。
那晚的夜色格外温柔,街面上的风儿轻轻拂动,心里想这事也如这空中的风,吹一吹,就会过去。
小孩子喜欢的东西都是一阵一阵的。
时隔一年,我住到乡下了,心心念念地种花种菜。在北京上幼儿园的茉莉,一有时间就会关注家里的植物与动物们,在视频里,满天星紫色的花里发出嗡嗡声,千里之外的她听见了。我告诉她是蜜蜂在采蜜。她隔空遥控,我蹲在地上,让手机摄像头在花丛里,移来又转去。这般劳神,仅仅只是好让她看清蜜蜂采蜜的姿态。老蹲着,挺累的,我站起来,她看到边上石缸里的鱼,瞬间情绪亢奋,嚷道:“奶奶,咱家啥时养鸭子?”
我吓得一惊,恨不得把手机扔了。
环顾四周,花草相间,角落里的两块菜地整整齐齐,要是两只鸭子来了,会怎样?很显然,茉莉还记得那个晚上我随口说的一句话。我哼哼哈哈想搪塞,可是茉莉的目光穿过大半个中国,追着我不放。
额头上的汗,心虚地往外淌,“现在是秋天,鸭崽崽要在春天,才能孵出来。”我讲了一个事实。
茉莉认真听着,然后抿了抿嘴,“那好吧,咱们明年春天养。”

四
养鸭子这事,在我家成了一件必须要做的事。
三月间,集市里就有鸭崽卖了,天太冷,我怕养不活。一拖,就到了四月,再不买,茉莉五一要回家度假了。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,我的脚步被那个看鸭鸭的小女孩缠住,自己的心也被鸭鸭们的憨态萌翻。潜意识里有个声音在重复:再不买回家,就要得罪茉莉了。这年头,我得罪谁都可以,独独不能得罪她,她的快乐可以逆流到我的血液里。鸭子会在园子里到处拉粑粑,臭气会招来蚊虫,那又怎么样,茉莉开心了,这些就都不成问题。
抱着这个信念,黄嘴巴与黑嘴巴被拎了回来。毋容置疑,黄嘴巴黑嘴巴都是拿鸭子的嘴巴说事,黄嘴巴整张嘴呈亮黄色,黑嘴巴呢,是棕橘色里接近嘴唇部位带点黑色。我统称它们的时候,喊它们臭鸭子。分别称呼的时候,就黄嘴巴黑嘴巴地叫。它们几乎形影不离,好事坏事一起干。比如把菜地里的秧子啄得干干净净,而且还不止一次,是连续三次恶意捣蛋。我举起棍子扑向它们时,茉莉的声音就在耳朵边响起“奶奶,有啥好恼的,不就是吃了些菜叶子呀。”
是啊,不就是吃了些菜叶子,可这些菜叶子是可以长成一棵棵辣椒树、茄子树、西红柿树的,上面要挂上夏季五彩斑斓的果实,还有丝瓜、黄瓜、苦瓜与南瓜的秧子本是要牵藤攀沿,然后瓜瓞绵绵的。这可是我搬到乡下住向往已久的景致,偏偏两只鸭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破坏,我即便是神也会举着竹棍,满院子追打它们。黄嘴巴黑嘴巴跑了一阵,索性不跑了,挤作一团,眼睛斜睨过来,似乎在说你打呀,举个棍子,虚张声势,又不真正扑打。
竹棍子扑还是会扑打下去,只是每次都是朝空地上扑。边扑边恶狠狠地诅咒:“臭鸭子,再吃我的菜秧子,我就会杀了你们,吃你们的肉。”
这句狠话不知咋地传到了北京。
茉莉打来视频电话,“奶奶呀,鸭子的听觉系统很好?百科绘本上说它们可以听到几千米远的声音。”“你说要吃鸭肉,它们听得见,它们还这么小,哪有肉可以吃。”我心说,它们能听懂就好了,再说了,鸭子长大了,本来就是人世间的一道菜,茉莉你不是挺爱吃北京烤鸭。当然我的反诘是在心里沉默。
茉莉又要我把视频对准鸭子,看它们在盆里嬉水。看着看着,她的圣旨到了:“奶奶呀,这盆好小,两只鸭鸭洗澡太挤了,咱换个大盆吧。”
我点头称是,说:“你小时候的洗澡盆,可以拿出来给它们用,盆就在杂屋里。”
茉莉停顿片刻,旋即一副大方相,嚷嚷:“拿出来吧,我早就不用了。”我心里哼哧哼哧,心想假如你妈给你来个弟弟或妹妹,我又得去买新的。
五
从黄花机场接回茉莉,正是午后鸭鸭休息时间。茉莉丢下行李,就去探望。只是黄嘴巴与黑嘴巴不懂礼数,它们趴在篾篓子里打着眼眯,茉莉与它们打招呼,它们却警惕起来,把身体往里边挪了又挪。
“慢慢来,”我与茉莉说,“熟悉了,就好了。”
“与它们视频了这么多次,还不熟吗?”茉莉反问。
这个问题天知道,我只能猜测,“鸭鸭可能看不懂视频。”
茉莉显然不相信。她告诉我,鸭鸭的视觉是“全景视觉”,它们能在不转动脑袋的情况下,能看见前、后、左、右的东西,还有头顶上整个天空。
想着都觉得不可能,人类眼睛的视觉都只能朝前看,背后的东西看不见。但我知道茉莉说得对,鸭子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,它们的视野范围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,还可以同时看清楚近处与远处的物体,最最神奇的是鸭子的眼睛,有三层眼皮,它们看到的图像是彩色的。
鸭鸭的眼睛这么厉害,并不意味着它们能看懂视频,能认识视频里的茉莉。它们厉害的眼睛,是用来在野外寻找食物躲避风险的。
茉莉表情悻悻,“它们与你熟吗?”她问。
“说不上,不过它们知道我管它们的吃喝,还不许它们进菜地捣乱。”
“奶奶呀,你管得太多了。”
“也是,奶奶正这样想着,从明天起,奶奶不管它们了,我把它们放到湖里去,它们想回家就回家,不回来,就让它们做野鸭子。”
茉莉觉得这主意不错。
第二天早上,茉莉走在前面,我提着鸭笼子,黑嘴巴黄嘴巴在笼子里惶恐不安,咿呀咿呀哼个不停。
“鸭鸭别叫了,一会你们就自由了。”茉莉回头对着鸭笼子说。
湖岸边的陆地上长满铜钱草,绿茵茵的,浅水边层层叠叠的菖蒲,剑一般指向空中,还有一丛丛的美人蕉,在石垒的围子里气势非凡。寻到一块纯粹的水域,在斜坡上把鸭笼子的门打开。黑嘴巴黄嘴巴没有马上走出来,而是一动不动地蜷曲在笼子里。我们退到湖边小路上。
万籁俱静。
春风从对岸树林刮来,两只白鹡鸰从一棵杨梅树上落到浮出水面的岩石上,边啄边鸣叫,然后跃入水中,把头扎进水里,划出水花。
就在这时,黑嘴巴从鸭笼子里探出了脑袋,斜着眼睛看了看天空,又看了看湖水,然后看了看立在路上不动的我们。一会,黄嘴巴也伸出了脑袋,它的神情似乎很愉悦,它悠然地迈出笼子,在草地上踱着方步,扇动着没长羽毛的翅膀,然后就与黑嘴巴一起低头觅食。没走几个来回,它们就直接往水里跳了,嘴里叽哩呱啦地唱起歌来。这之前,它们只在盆里玩过水,眼前宽阔的水域,风里漾起的水纹,一圈来了一波又走了,浮力还时不时让鸭鸭全身摇晃,它们黄色扁脚划动两下,又妥妥地坐在水上。鸭鸭好生好奇,小心翼翼地,沿着水岸线,走走停停,在石头缝、水草里啄虫子与嫩草芽。游着游着,它们忽然把头栽进水里,湖里的小鱼小虾多是多,它们基因里是自带捕捉本领的。(此为节选版本,更多精彩请参看纸质刊物)
刊于《湘江文艺》2024年第6期。
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。

万宁简介:湖南岳阳人。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等刊物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,作品被多家选刊多个选本选载,已出版《城堡之外》《麻将》《纸牌》《讲述》等。